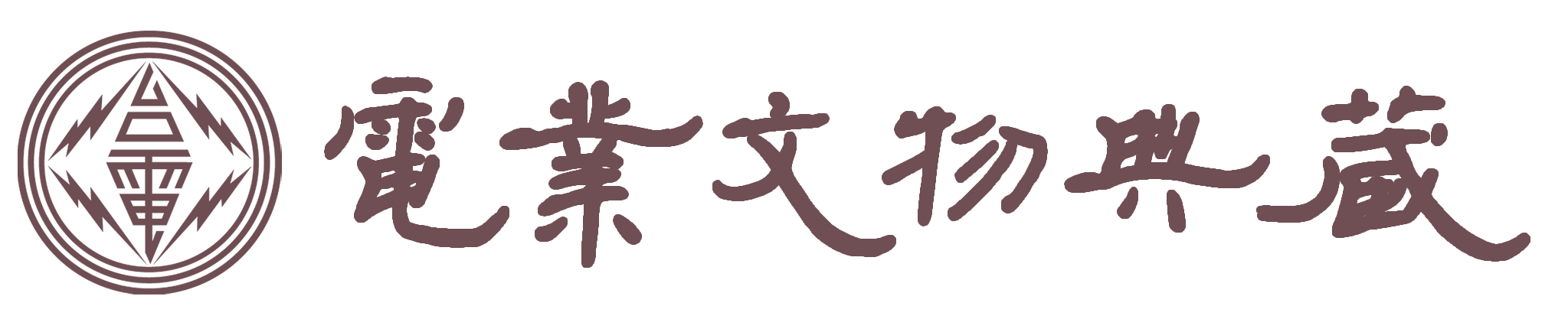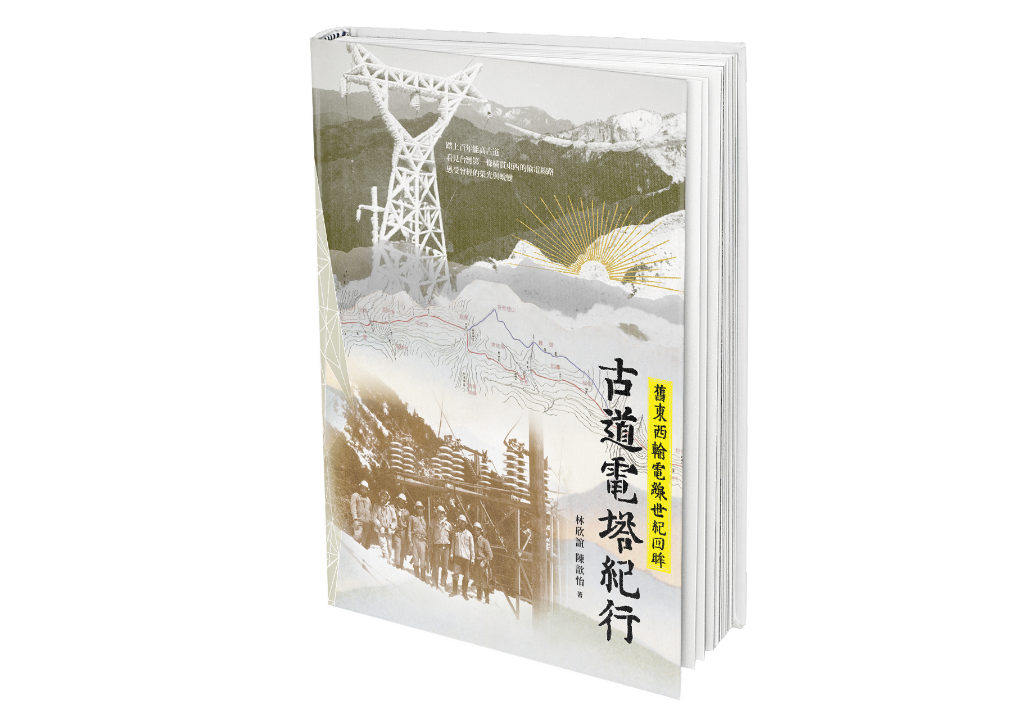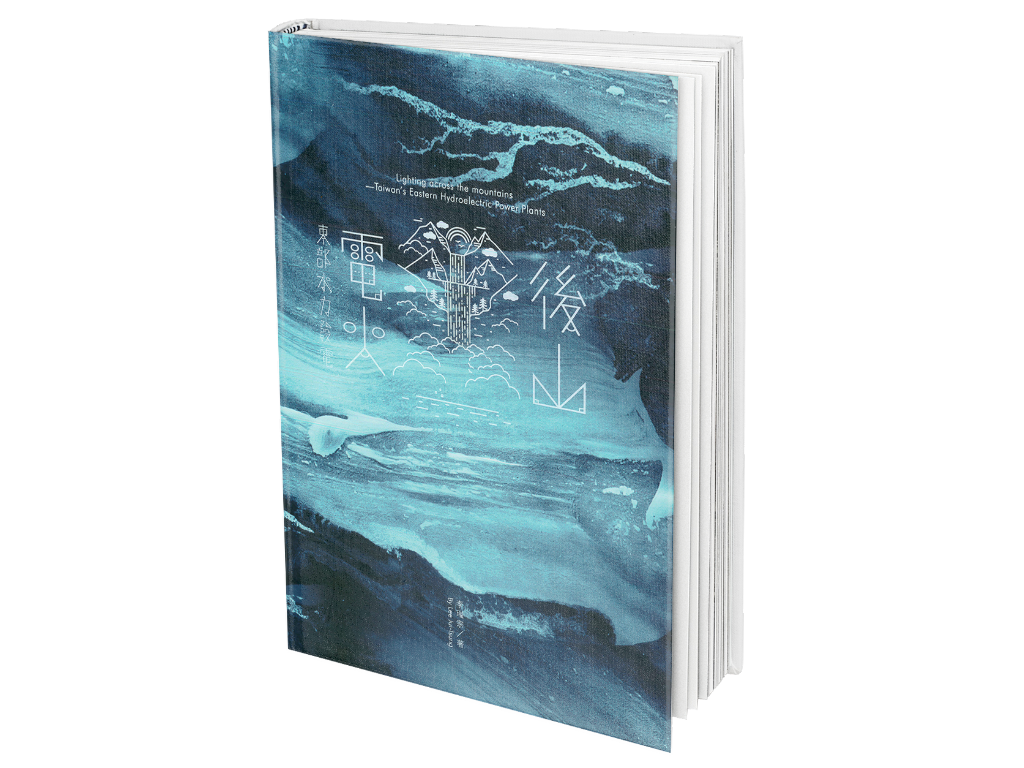撰稿 謝易軒
光彩耀眼的碧海藍天、綿延數里的金色沙灘、世界級的地質奇景,與南島特殊的風土人情……澎湖的美,讓到訪此地的遊客難以忘懷。更有不少澎湖的在地子弟,希望能夠留在家鄉成家立業。無奈,由於工作機會不足,許多成長於澎湖的年輕人即便希望留下,只能選擇離開美麗的澎湖灣。
台灣電力公司位於澎湖的尖山發電廠,提供了一個聰明的方法,讓更多澎湖孩子有機會根留故鄉。
產學合作,台電工作機會延緩人口外流
落成於民國 91 年的尖山發電廠,是澎湖目前唯一的火力發電廠。接續原澎湖電廠,尖山發電廠供應島上逐年增加的用電需求。
過去,要留住駐派澎湖的電廠專業人員,並非容易的事,台電於是開始鼓勵並培訓澎湖當地人力進入台電服務。數十年間,台電持續提供「台電特別助學金」及「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獎學金」,鼓勵澎湖本地家境清寒、成績優秀的孩子專注課業,並與澎湖高級海事水產學校(後簡稱澎湖海事學校)產學合作,開出保送名額,讓校內成績優異的畢業生直接進入台電工作。澎湖海事學校的學生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長的澎湖孩子,對於想要留在故鄉的學子來說,這不啻絕佳的工作機會。
尖山發電廠的領班趙崇瑋自民國 80 年從澎湖海事學校畢業後,就因為台電獎學金而進入台電工作,至今已經超過三十個年頭。如今他在柴油機課工作班帶領年輕的台電員工,負責機組維修與每年的歲修工作,他所教導、帶領的許多後生與同仁,都是澎湖海事學校畢業的學弟學妹。
延攬優秀在地學子,台電喜獲穩定人才
「在澎湖海事成績非常績優的孩子,才有機會進台電。」澎湖海事學校校長彭閔淵說,保送生基本都能同時考上頂尖的國立大學,但最後幾乎都選擇台電。這些年輕員工在學期間就接觸柴油機與輔機、鉗工、車床等相關課程,畢業後經由保送計畫進入台電的營業處或尖山發電廠工作。有的員工表示,自己一方面希望分擔家中經濟負擔,另一方面也想留在澎湖,而台電剛好提供了兩全其美的機會。
對台電來說,在地學子保送計畫不只是造福澎湖的在地青年,也提供自家尖山發電廠穩定的人力資源。來自澎湖當地的員工流動性低,用人當地化不僅維持電廠穩定,更有利於台電柴油機核心技術的保留與傳承。
如今,尖山發電廠近一半的的員工都畢業自澎湖海事學校。
不僅如此,民國 95 年起,台電尖山發電廠成立澎水校友會, 同時設立「台電尖山電廠澎水校友會清寒獎助學金」,由任職於尖山發電廠的澎湖海事校友自發樂捐,資助家境清寒而學業優秀的學弟學妹,獎學金發放對象不限電廠相關科系,這使台電公司與澎湖海事學校的合作不僅持續為雙方加分,並造福更多元的澎湖學子。
橘色磚牆、藍瓦屋頂,和三支聳立的七彩煙囪遙望著尖山海灘,各自繽紛。台電尖山發電廠已是澎湖獨特而不可或缺的一隅風景,未來也將持續提供穩定可靠的能源,陪伴著澎湖的孩子一起成長。
本篇搭配影片:
你可能有興趣
【臺灣百年電業史話25】永續發展
作者:許伯瑜 當你睜眼醒來,打開電燈、冷氣、手機、音響、電腦——無數個小小的電源開關被開啟,電力點亮了一天的生活。你有想過這些能源從何而來?背後藏著什麼的能源故事、又有多少便利與環保間的掙扎呢?你希望你使用的「電」是以經濟效益為導向,便利又低廉;或是以社會責任為導向,對社會環境更友善呢? 強調永續經營時代,以專業落實共好願景 各行各業競爭激烈、各式宣傳百花齊放,除了既有產品與服務品質極為重要外,企業也試著擴大自己品牌對社會的影響力——提倡環保、投入公益、永續經營。從CSR、ESG與SDGs種種行動呼籲與績效指標的出現可以發現,當今企業不再只以營利為目標,也試著對社會有所貢獻。 台灣電力公司作為臺灣的最大的能源企業,在發展電力事業服務民眾的同時,也須考量其決策對自然環境與社會大眾的影響。如何取得平衡,也成為台電公司的大哉問。事實上,台電也正持續以自己的專業與文化歷史,落實「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願景。 台電官網設置「永續發展專區」,其中包括企業「ESG發展圖像」的完整說明,並提供《永續報告書》、《SDGs報告書》供讀者參閱。(圖像來源:台電官網) 維繫人類生活,兼容生態永續 電力事業的發展往往和自然息息相關,即便是近年來國內外開始採用的綠能發電,對於自然生態仍可能影響甚鉅。以風能為例,看似潔凈的風力能源,對於蝙蝠這樣的動物而言,卻可能造成生存危機。 蝙蝠可以捕食害蟲、幫助植物授粉或傳播種子,在自然界是維繫生態與糧食安全的重要角色。臺灣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與環境,使得蝙蝠物種多樣性極高。然而,由於風力發電機與蝙蝠的飛行高度接近,容易造成大量的蝙蝠傷亡。這是因為風機扇葉運轉末端時速高達300公里,撞上它就相當於撞上行駛中的高鐵,國內外都有蝙蝠撞上風機而死亡的案例。 取得能源不是沒有代價,人們也不應該選擇視而不見。所以台電選擇用每一次調整,讓犧牲越來越少。 在雲林臺西,為了規劃風力發電站,台電啟動「蝙蝠棲地搬遷計畫」,於風場周邊設置蝙蝠巢箱,引導蝙蝠遷移至風場南側新棲地,打造「共生共融」的生態電廠。電廠在興建時亦避開蝙蝠繁殖的季節,採分區分段進行工程;同時也設有感應系統,風機運轉時如果偵測到周遭有鳥類或蝙蝠群體,可遠端控制降載甚至停機,在供電的同時也守護動物們的安全。 生態電廠不但能減少開發衝擊、保育物種與棲地,也重新定義電廠與土地的關係,成為兼具供電、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功能的場域。目前台電已有八處生態電廠,守護珊瑚、紫斑蝶、東亞家蝠、黑面琵鷺與臺灣大豆等動植物。發電的同時亦兼顧棲地營造、保種復育與生態維護,為臺灣生態環境盡一份心力。 台電於 2024 年環境月製作的「八大電廠明星物種生態地圖」,展示了全臺各地電廠周邊豐富的自然生物樣態。(圖像來源:台電Energy OMNI網站) 保護歷史遺存,留下故事線索 台電除了運用自身專業,透過打造生態電廠落實環境永續,也積極在社會中扮演文化保存的角色。台電前身為 1919 年成立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走過百年歲月,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留下許多歷史記憶,見證了臺灣電業的發展。其中有許多故事,都值得被留存與傳承。 近年來,台電呼應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及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公約,積極推動電業文化資產保存的相關工作。以「先典藏研究,後展示教育」為方針,透過古物調查、口述歷史、專書出版,爬梳臺灣電業的發展脈絡。 從配電技術的演進、河川流域與水力發電的關係、離島電業的發展甚至是台電球隊的歷史,百年電力史不是冷硬的技術圖表,而是與土地、河流與生活息息相關,台電以不同議題進行文物清查與徵集整合文史資源,並積極辦理各類文資活動與文化策展。 2024 年,台電更進一步啟用「台灣電力文物典藏中心」,藉由文物保存來為臺灣電業發展史留下紀錄,而「電業文物典藏網」也成為一個歷史文化的交流平臺,開放已數位化的文物之餘,也進行文史科普,促進社會大眾對於臺灣電業文化的近用性。 2024 年台電啟用的「台灣電力文物典藏中心」,妥善收藏台灣電業史上的重要文物。(圖像來源:台電官網) 善盡社會責任,達成共好共榮 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台電如何在永續與教育之間找到平衡,不妨親自走進板橋車站旁的「TAIPOWER D/S ONE 電幻1號所」。它不只是展示空間,更像是一場關於能源未來的生活實驗。在理念上,它將原本的「配電」(Distribution)、「變電」(Substation)轉譯為「Design」(設計)及「Sustainability」(永續)的全新概念,成為向社會大眾發聲的窗口。 無論是「ENERGYM能源健身房」裡邊運動邊發電的趣味體驗,或是「POWERLAB創客空間」中跨界創作者的綠能藝術實驗,台電除了爬梳自身的歷史文化以外,也同時以互動、科技與創意翻轉了大眾對電力企業的想像。 面對自然生態、社會大眾,台電善盡與關係人溝通的責任,不僅盡心成為「永續電力」的發電者,更以行動成為推動社會共好的夥伴。從生態電廠的共融設計到電幻1號所的教育推廣,台電以專業實踐永續理念,將「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化為日常。 儘管當今全球能源企業仍面臨轉型過程中的諸多挑戰與社會質疑,但台電選擇直面困境,並試著找出共好共榮的方式。未來,台電將持續以創新、責任與關懷為核心,點亮臺灣每一處,也點亮全民對未來的想像。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台電 2024 環境月首播全台最大規模蝙蝠研究 八大電廠明星物種生態地圖首公開〉,Energy OMNI 網站,2024年4月26日 發布。 〈台灣電力文物典藏中心今開幕 收藏近1600件文物〉,台灣電力公司網站,2025年10月22日發布。 吳佩旻,〈ESG是什麼?與CSR、SDGs差在哪?企業、投資人都該懂的3個關鍵字〉,天下雜誌網站,2025年9月18日發布。 胡華勝,〈生態電廠新典範!雲林台西風電廠,為何幫蝙蝠們搬新家?〉,遠見雜誌網站,2024年5月7日發布。 楊語芸、孫維揚,〈台灣風機造成蝙蝠大量死亡,比歐美高出十倍,專家:應導入「智慧降載」保護蝙蝠〉,上下游新聞網站,2022年3月10日發布。 蘇怡如,〈文化藝術、文資與電力的嶄新火花——訪台灣電力公司〉,國藝會藝企網,2021年6月23日發布。
2025.11.30
東西輸電線的建設基礎,竟是日治時代的熱門登山路線?
在臺灣,喜愛爬山的人必定都知道「能高越嶺道」。這條橫越臺灣中部山區的道路,沿途風光明媚,曾吸引無數國內外的登山客前往朝聖。 1917 年由日本政府動工興修的能高越嶺道,是為了監控山區情況而設置的「警備道路」。不過,它的東部路段,在 1925 年曾經過修改。原先的「舊道」必須越過奇萊山區,海拔高度達到 3,307 公尺。改道後,人們只需登上海拔 2,800 公尺左右的「能高鞍部」,就能跨越中央山脈 —— 這條「新道」的攀登難度,顯然比「舊道」友善許多。能高越嶺道的登山健行風氣,大抵也就從這個時期開始,漸漸醞釀成形。 佐藤春吉與他的旅行紀實 1926 年 7 月,臺北第一中學(即今日建國中學)的教師佐藤春吉率領著 10 名日籍學生從南投霧社出發,循著能高越嶺道的「新道」,徒步走完四天行程。翌年,他將這次的登山經驗寫成文章,發表在剛剛創刊的《臺灣山岳》雜誌。 佐藤春吉的文章,提示了旅途中的交通、住宿等種種實用細節,可說是一份詳盡的旅行指引。更重要的是,透過他的紀實性描述,許多讀者都發現這條陌生山徑並不可怕,沿途更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華麗美景。 同一時期,日本政府也積極在臺灣推廣登山活動,許多學校也紛紛成立同好社團,喜好爬山的人群逐漸增加。這些登山愛好者,自然也想要循著佐藤春吉的指引,前往能高越嶺道一探究竟。 佐藤春吉的旅行紀實〈能高越〉,與刊登該文的《臺灣山岳》雜誌創刊號封面。(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 1930 年代的登山風氣 1930 年的「霧社事件」,使得臺灣中部的山林,一度籠罩在殺戮的陰影之中。但在事件平息後,能高越嶺道上的人潮很快又恢復過來。此外,隨著「國立公園」的倡議興起,臺灣的山林美景,又進一步透過廣告宣傳被更多人所看見,登山風氣也跟著助長不少。 由於登山隊伍漸漸增加,使得警察機關必須在能高越嶺道上挪出數個警察「駐在所」,將之設定為「指定宿泊地」,為登山客提供住宿服務與簡單飲食。設備越完善,對於普遍民眾而言也更容易親近。日治晚期,攀登能高越嶺道的行程,已被收錄在一些大眾導向的旅遊手冊當中,可見這條登山路線變得越來越普及化。 日治時期設置於能高越嶺道上的「能高駐在所」,被譽為「檜木御殿」。它的建築規模宏大、設施齊備,對於早期的登山客而言是重要基地。(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東西輸電線與保線所 二戰來臨後,臺灣的社會大眾自然無心登山,能高越嶺道也在 1940 年代中期因為自然侵蝕而嚴重損毀。直到 1950 年,台灣電力公司決定沿用日治末期的計畫,循著能高越嶺道建設「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將花蓮地區水力電廠生產的剩餘電力送往臺灣其他地方,這條道路才迎來修復契機。 東西輸電線完工後,能高越嶺道也成為台電「保線員」的工作道路,原先分布於沿線的一些警察駐在所亦變更用途,成為「保線所」(亦即保線員的工作站)。 1950 年代以來,能高越嶺道的登山風氣復甦,這些保線所也成為登山客經常借宿的地方。其中,「天池保線所」更在 1986 年重建為「天池山莊」,成為專門的山屋。近年來,「檜林保線所」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接管後,也將重新規劃為住宿場所,繼續為山友提供服務。 1953年為了紀念東西輸電線竣工而建設的「光被八表」紀念碑,後來也成為能高越嶺道上的著名景點。近年來,紀念碑已在自然力量的侵蝕之下斷裂,如今仍以遺跡形式保留於原址。(圖像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能高越嶺道的百年故事 回顧能高越嶺道的歷史,最初它是日本時代的警備道路,後來又成為東西輸電線的建設基礎。與此同時,登山風氣的興起,更驅使人們走進山林,讓它變得越來越熱鬧。 包括東西輸電線在內,過往歷史的諸多遺跡,迄今仍是能高越嶺道的沿線風景。下次,若你有機會造訪這條山中古道,不妨仔細留意路旁的種種線索。除了雲瀑、斷崖等等壯麗風景之外,或許你也會在旅行途中,驀然看見這條道路百年來的歲月變遷、盛衰起伏。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員林務局,2011),頁226-241。 佐藤春吉,〈能高越〉,《台灣山岳》,1(臺北,1926),頁 50-62 。
2025.08.04
臺灣近代大規模水力發電系統的開端——濁水溪(日月潭)的電業文化路徑(下篇)
作者:簡佑丞(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三、循著濁水溪「電業文化路徑」探訪「活的」臺灣電力文化資產 在「走讀」由歷史發展歷程、脈絡以及流域整體的水力發電運作體系所形成、建構的濁水溪電業文化路徑後,讓我們換個方式,透過地圖、沿著濁水溪流域由下而上,依序實地探訪系統性串聯、組構成的濁水溪水力發電體系之各主要建築物、構造物設施。 事實上,一個體系化之水力發電系統群的形成(構成)與整體河川流域的水資源運用密不可分。其系統性的運作方式通常於河川流域上游設置水資源取水、導水與蓄水(水庫)等「水資源設施」,並在其下游處(相對海拔較低處)設置「水力發電設施(群)」(發電廠),利用水位落差進行發電,發電後的尾水又供更下游的發電廠發電,流域水力資源的持續循環利用,建構了以河川流域為核心的完整水力發電系統群,也形成了以河川流域為中心的電業文化路徑。濁水溪電業文化路徑亦是如此,因此接下來跟著筆者的腳步以溯源的方式,由濁水溪中下游的「水力發電設施(群)」,一路上溯至發電體系源頭的「水資源設施」。 日月潭水力發電設施群 ■水力發電廠設施(群) ① 烏塗電廠─新舊並存的水力電廠 沿著濁水溪左岸至流域下游與中游分界點的雲林縣林內鄉烏塗村,靠近農水署雲林管理處農田水利文物陳列館與嘉南大圳濁幹線八卦池不遠處,即可看見一座單面斜屋頂造型的紅色建築物。這是於1922年建成、原作為嘉南大圳烏山頭水庫大壩施工機械用電的烏塗水力發電廠(舊稱濁水水力發電所)。該電廠建築在設計之初為順應濁幹線導水路堤防,並與其共構,才會有此造型特殊的斜面屋頂設計。磚造結構的建物,整體外觀兼具歷史與現代主義的折衷樣式,特別是下半部帶有古典風格的拱型長窗,以及上半部具早期現代主義幾何造型的圓窗,讓強調功能性設計的電廠建築顯現出獨特趣味。其內部設置的三臺水力發電機組則是日本京都奧村電機製作的產品。 烏塗電廠在嘉南大圳完工後轉讓予臺灣電力會社,戰後由台電公司繼承,並改供斗六糖廠製糖產業用電。1999年,921震災造成廠房內外多處裂縫,雖經修補,但古舊建築的耐震度已出現疑慮。2004年,該電廠被雲林縣政府指定為縣定古蹟後,隔年便停止運轉除役,未來擬修復活化為水力發電博物館。與此同時,台灣電力公司於2003年起在烏塗電廠左側另建仿舊電廠建築意象的新電廠,並利用原有發電所的前池(水壓槽)與沉砂池設備,以集集攔河堰南幹渠的水源取水發電。如此新舊發電廠並存的方式,不僅繼續維持水力發電與農業灌溉的水資源運用外,也保存了具歷史、技術價值與意義的電力文化資產。同時也成為一個展現水利文化資產系統性、整體性、脈絡性與永續性價值的範例。 烏塗電廠(舊濁水水力發電所)現況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烏塗電廠(舊濁水水力發電所)完工舊照 資料來源:嘉南大圳工事寫真帖(1922) 烏塗電廠(舊濁水水力發電所)內部發電機組舊照 資料來源:嘉南大圳工事寫真帖(1922) ② 鉅工電廠與明潭水庫(明潭發電廠) 離開烏塗電廠後,繼續沿著濁水溪流域往中、上游河谷前行,經過南投縣的集集小鎮後便抵達水里。從集集線水里車站向濁水溪對岸望去,便可看到黃褐色外觀的長方體建築,其後還有從山頂冒出的兩根醒目長條型大水管,一路貼著山坡向下延伸至建物身後。這棟背後連著兩條綠色大水管的建築就是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鉅工電廠前身)。該電廠利用身後的兩根巨型水管將第一發電所發電後排出的尾水,經銃櫃壩蓄水調整後透過高低落差引入廠內的發電機組發電,發電後的尾水再排入濁水溪支流水里溪中。 鉅工電廠建築於二戰末期,曾因美軍大規模空襲而遭受嚴重破壞。戰後,台灣電力公司將之修復,才恢復昔日樣貌。1946年10月,當時的總統蔣中正偕夫人蔣宋美齡女士前來視察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設施的復原狀況,該電廠由蔣宋美齡女士親題「鉅工」,從而由戰前的第二發電所改為今日所稱之鉅工電廠。當時作為第二發電所調整池的鋼筋混凝土拱重力壩──銃櫃壩施工時,需要製冰設備冷卻混凝土,1937年銃櫃壩完工後,便將此冷卻設備轉為生產枝仔冰,作為職工福利的一部分,並且逐漸成為有名的台電「二坪枝仔冰」。 由鉅工電廠循著水里溪溯源而上,便抵達林業製材聚落──車埕。來到此地,大家的關注焦點應該都是車埕老街,以及由舊大雪山林業公司製材工廠修復活化的車埕木業展示館吧!不過,在參觀的同時,大家很難忽略矗立在展示館旁舊儲木池前方有如混凝土巨牆的龐然大物。這座龐然大物即為明潭水庫的下池壩,而水壩旁隱身在山壁內部的便是排名世界前十大的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廠。該電廠是將山壁挖空,利用其內部空間設置的地下電廠,故從外觀無法窺見其全貌。當白天用電尖峰時,便自海拔較高的日月潭引水至海拔較低的明潭發電廠發電,並將發電後尾水匯入明潭水庫儲存,等到夜間用電量較小時,再利用夜間剩餘電力將明潭水庫的水抽回日月潭繼續循環利用發電,這就是抽蓄發電的原理。也因此,大家可能會發現為什麼有時候白天和晚上的日月潭水位落差如此之大,就是因為電廠正在進行抽蓄發電呢!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原始資料:臺灣日日新報(1937.8.26) 鉅工電廠現況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23) 車埕聚落、明潭下池壩與明潭水庫空照全景 資料來源:台電綠網網站https://service.taipower.com.tw/greennet/ecofriendly/education/location/91 ③ 大觀發電廠與明湖水庫(大觀二廠) 從車埕繼續沿著濁水溪流域支流水里溪而上,就可抵達前身為日月潭第一發電所的大觀電廠。該電廠可謂戰前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的核心發電設施,日月潭儲蓄的湖水便是經由其主建築背後連著的五根巨大鋼管引流自電廠內發電,瓩最大可產生10萬(kW)的電力,當時可供應全臺所需電力外還綽綽有餘。不過,該電廠和前述的鉅工電廠相同,在二戰末期遭到美軍大規模的空襲而損壞嚴重,戰後經台電公司積極修復後才終於恢復昔日樣貌,並在1946年10月由前來視察的總統蔣中正改命名為「大觀發電廠」。完工百年後的今日,大觀電廠與鉅工電廠依舊持續運作,共同肩負起臺灣電力供給的使命。 而在大觀電廠右側不遠處聳立的巨大鋼筋混凝土大壩則是明湖水庫,水庫旁山壁內部便是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廠(現稱大觀二廠)。和前述的明潭電廠一樣,明湖電廠也是設置於挖空山體內部的地下抽蓄式水力電廠,而且還是全臺抽蓄式水力電廠的始祖。當初委由德國與瑞士的顧問公司協助規劃設計,並由榮工處負責工程施工。由於明湖電廠的成功經驗,讓臺灣得以在此基礎上接續完成當時亞洲規模最大的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廠。 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大觀發電廠)完工舊照 資料來源: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と其現況,土木建築工事畫報,昭和8年8月號(1934.8) 大觀發電廠現況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23) 明湖水庫現況全景,右前方即為大觀發電廠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大觀發電廠 ■發電水庫(水資源)設施 ④ 日月潭的地標─水社壩與工程殉難紀念碑 自明湖水庫沿著131縣道經過南投縣魚池鄉後便進入知名的日月潭風景區。順著臺21線往右,映入眼簾的是設立在湖岸、刻有日月潭三個大字的石碑。石碑後盡是開闊的湖面與設有木棧道的斜坡草地,為一覽日月潭湖光山色的最佳地點。不過,大家所站立的這片視野絕佳之斜坡草地,其實是人為築造的土石壩體──水社壩。原本該處為日月潭水源向外溢流的水社溪谷,當時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為利用日月潭作為蓄留更多發電用水資源的水庫,遂規劃於此興建水社壩,以便提高日月潭的水位,儲蓄更多引自濁水溪上游的水源。 事實上,原先水社壩採用1920年代流行於美國西部的RC重力式複拱壩型式設計,但後來因工程技術與耐震問題而放棄,改採用土石壩興建而成為今日所見與大地、自然調和的景觀樣貌。在水社壩底端一側,尚有當時承包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鐵道工業株式會社」,為紀念從1931年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開工到1934年完工期間,因故殉職的臺籍職工而設立之「殉難碑」。透過紀念碑後刻記的多位殉職人員姓名與詳細資訊,讓人遙想當年建設工程之浩大與艱辛。 接近完工的水社壩舊照 資料來源:日月潭發電事業ノ大要(1934) 水社壩現況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23) ⑤ 鷹眼天井奇景之謎─溢流井 在水社壩一側、日月潭碑石附近的湖岸邊,可以看到一座突出於湖水中的奇特圓塔狀構造物。事實上該構造物從上空俯瞰空拍而呈現有如鷹眼天井的謎樣奇景,還曾被各大新聞媒體報導一番。其實這座造型奇特的謎樣構造物是日月潭的溢流井,當日月潭水位過高時,為了不讓湖水越過水社壩頂而恐造成水壩潰決崩塌,便須透過溢流井將過多的水排除。我們可以試想有如一個洗臉盆(或洗手槽),當洗臉盆的水位過高時可透過上方的溢流孔將水排除以避免盆內的水溢流,日月潭的溢流井就猶如洗臉盆的溢流孔功能,是保護日月潭水庫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接近完工的日月潭溢流井舊照 資料來源:日月潭發電事業ノ大要(1934) 日月潭溢流井現況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23) ⑥ 引濁水溪水入日月潭的關鍵─武界壩 最後則是遠離日月潭,上溯濁水溪流域上游的仁愛鄉武界部落,從部落隔著濁水溪對岸往上不遠處,即是戰前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的重要設施──武界壩。由於最初的日月潭為一水位不深的天然湖泊,其水量不足以供給水力發電用水之需,因此當時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便計畫於濁水溪上游興建一座攔水壩,利用濁水溪上游豐沛的水資源,將溪水透過導水隧道穿越重山峻嶺後引入日月潭蓄存足夠的發電水量。原先選定的地點為姊妹之原,爾後因考量濁水溪含沙量高,該處河道地形空間不足以長時間容納泥沙的沉澱量,最終改以武界作為水壩的建設地點。 武界壩興建當時,負責現場工程的鹿島組(今日本鹿島建設公司)為克服崎嶇地形限制導致水壩結構混凝土灌漿施工的難題,負責的工程師便發揮創意,在武界壩所在兩側峽谷壁上架設吊橋,利用吊橋與懸吊在其上的輸送管線將已預拌好之混凝土運送到指定位置,從上沿著輸送管澆灌至下面壩體之預定位置,如此作法大大增加施工的效率,使武界壩能順利興建完成。時至今日,武界壩仍然堅守攔蓄濁水溪上游水資源,並將溪水引入日月潭的重責大任! 混凝土澆置施工中的武界壩舊照(左)、剛完工的武界壩舊照(右) 資料來源:台灣の水利(1933)、日月潭發電事業ノ大要(1934) 武界壩現況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2024.09.30
誰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風力發電機?
作者:陳韋聿 隨著綠能建設的迅速開展,風力發電機已成為臺灣能源轉型的重要支柱。看著巨大的風機扇葉在風場中呼嘯運轉,我們不免會疑惑:究竟是誰那樣聰明,率先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風力發電裝置呢? - 在中文世界的網路資料當中,這問題的解答可謂眾說紛紜。有些文章將功勞歸給蘇格蘭人布萊斯(James Blyth),有些則說是美國人布拉許(Charles Brush)或丹麥人拉庫爾(Poul La Cour)。實際上,這三個名字,各自都代表了風力發電的某個技術演進階段。 1890 年代,拉庫爾針對風機進行的系統性改良(稱為 “Kratostate” ),解決了風力忽大忽小、電能轉換也跟著不穩定的關鍵問題。此外,他所設計的風機,也更趨近於今天廣泛被運用的風機形式。因此,拉庫爾被尊稱為「現代風能之父」。 布萊斯與布拉許的發明,出現的時間則要比拉庫爾更早一點。 1887 年,這兩個人都在自家院子裡建造了一具形狀特殊的風力發電機,雖然發電效率仍差強人意,但他們的嘗試,向世人證明了「風力發電」確實可行。值得注意的是:布萊斯的風機在 1887 年的 7 月開始運作,布拉許的風機則得等到當年冬天才完成。單就時間順序而言,布萊斯或許才是真正的勝利者。 由左至右,分別為布萊斯、布拉許、拉庫爾所設計的風力發電機。 那麼,「史上第一部風機」的發明者,果真就是布萊斯嗎?恐怕還不一定。 近年來,法國的風電史研究者布魯耶爾(Philippe Bruyèrre),提出了一個更早的答案。他指出:早在 1883 年舉行於奧地利維也納的國際電力博覽會當中,來自奧地利的發明家弗里德蘭德(Josef Friedländer),已經將一部抽水用的風力渦輪機改造成發電機組。而且,在現存的展場設計圖當中,我們還能見到這部風機俯視與側視的圖繪資料! 2022 年,布魯耶爾將他的發現,闡述在一本名為《復古未來》(Rétrofutur : une autre histoire des machines à vent)的法文著作當中,透過美國作家吉佩(Paul Gipe)所撰寫的書介,這些研究成果得以被更多人看見。 總而言之,關於「誰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風力發電機」這個問題,目前我們所知的最新答案,是奧地利人弗里德蘭德。然而,隨著歷史研究的持續推進,這個說法,或許有一天也會遭到推翻 —— 根據一些冷門文獻的說法, 1876 年美國費城的世界博覽會裡,也曾出現過一部「多金屬葉片的(風力)渦輪機」(many‐blade sheet metal turbine)。那部機器,會不會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風力發電機呢?恐怕還得等待更多的證據出現,才會有確切的解答了! 布魯耶爾曾在 2021 年贏得科技史的重要獎項 Turriano ICOHTEC Prize,是相當傑出的學者。(圖像引用自 Paleo-Energetique 網站) 參考資料 Brandon Owens, The Wind Power Story: A Century of Innovation That Reshaped the Global Energy Landscape (New York: Wiley-IEEE Press, 2019), pp. 1-12 Paul Gipe, “Austrian was First with Wind-Electric Turbine Not Byth or de Goyon,” WindWorks.org, July 25, 2023.
2025.02.21
來自希臘神話的能量加持?台電球隊的隊徽設計
太陽神阿波羅、海神波賽頓、智慧與戰爭之神雅典娜——你一定聽過這些神祇的名字,對嗎? 在西方文化當中,希臘神話廣泛受到大眾喜愛,故事裡的神祇各自代表著某種力量,也因此,這些神祇經常被引用到各種體育隊伍的形象設計之中。像是著名的歐洲職業足球隊阿賈克斯(AFC Ajax),隊伍名稱就取用了特洛伊神話裡一位戰爭英雄的名字,它的隊徽也呈現了這位神話英雄的形象。 荷蘭職業足球隊阿賈克斯的隊徽設計,引用自特洛伊神話的戰爭英雄阿賈克斯。(圖像來源:Wikimedia) 在臺灣,也有許多競技隊伍曾以「戰神」、「海神」、「太陽神」為名,並且同樣將這些西防神祇的形象,轉化為隊徽設計的創作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台電公司也仿效這樣的作法,重新設計了旗下六支球隊的隊徽,並且為每一支隊伍安排了能夠與之呼應的希臘神祇。像是排球員的殺球動作,就像手持閃電的希臘勇士;足球員的射門,則像是掀起滔天巨浪的大海王者…… 新版的隊徽設計,結合了神祇形象與運動類型。同時,也希望透過這些神祇各自代表的寓意,來為場上拚戰的運動員賦予力量。像是台電女籃的天神宙斯,象徵著「力量」、「勇敢」、「勝利」;台電女羽的勝利之神妮克,則代表「專注」、「自信」、「卓越」。 如果讓你來選的話,你會想要讓哪一個天神,來為你自己喜歡的球隊賦予能量呢?一起來想想看吧! 台電旗下六支球隊的logo設計。(圖像來源:台電公司網站)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賴佳吟,〈新視野 新世紀 嶄新Logo再現 台電球隊再出發〉,《台電月刊》,667(2018.7),頁24-25。
2024.07.23
安全第一:電廠安全標語的小歷史
作者:陳韋聿 走進高雄的台電「南部發電廠」,我們立刻可以看到建築物上高懸著「安全第一」四個紅色大字。在早期的發電廠、變電所等電力相關場域,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到這句標語。不過你知道嗎?「安全第一」其實也是有歷史的! 「安全第一」( Safety First )這句話,起源自20世紀初期。當時,美國鋼鐵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的創始人 Elbert Henry Gary 有感於工安意外頻傳,奪走無數基層工人的性命,決心要創造安全至上的嶄新企業文化。於是,「安全第一」成了美國鋼鐵公司的經營原則,同一時期,隨著勞工階級的職場待遇在美國漸受重視,整個工業領域裡的其他公司也紛紛仿效 Elbert Henry Gary 的做法,導入「安全第一」的觀念。 就這樣,「 Safety First 」這句標語,也就從這個時代開始大為流行,並且隨著美國工業的勃興,進一步傳播到海外各地。影響所及, 1912 年的日本,也開始出現所謂「安全專一」的倡議以及標語。之後,這句話逐漸演變成「安全第一」,除了在日本的實業界廣為流行以外,在臺灣的發電廠、工廠等等廠房當中,也經常能夠見到。 你也在其他地方見過「安全第一」的標語嗎?下次讀到這句話,或許你也會想起一百年前 Elbert Henry Gary 體恤勞工的苦心喔! 台電南部發電廠外牆上的「安全第一」標語。(圖像來源:工研院節能標竿網) 1925年美國一家工廠裡的「Safety First」標語。(圖像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新井充,〈「安全第一」“Safety First”「安全専一」〉,《安全工学》,55:1(東京,2016),頁1。
2024.04.29
停電的副作用竟然是缺米?日治初期臺灣民生產業的電力依賴
提起「工業用電」,你可能會想到科學園區、煉鋼廠、煉油廠裡頭轟隆隆運轉的機械設備。不過,在百餘年前的臺灣,這些產業多半都還沒有誕生,各個發電廠所生產的電力主要仍是用來點亮燈炮、運轉電扇,工業用電僅只佔去一小部分。問題是,在日治時代前期,什麼樣的產業會需要使用電力呢? 以1909年底開始供電的「竹仔門發電所」為例,在1910年代前期,該電廠所供應的工業用電,主要的使用者是輾米廠與製冰廠。傳統時代,碾米所使用的笨重器械,主要倚賴人力、畜力或者水力來帶動。直到日治初期引進了電力碾米設備(米絞仔),相關工作才變得輕省許多。不過,由於碾米廠高度仰賴電力,當「竹仔門發電所」因為颱風等災害而停電的時候,市場上還可能因此鬧米荒呢! 另外,製冰技術同樣在日治初期引入臺灣。在電冰箱還不普及的時代,冰塊對於食物的保鮮有極大助益,對於這座位處亞熱帶的島嶼而言是迫切需求。而如果製冰廠同樣受到停電影響,導致冰塊停產的話,南臺灣的菜市場,可能也會因此而瀰漫著食物腐臭的味道吧! 日治時期的旗山碾米廠。(圖像來源: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文化資產網)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吳政憲,〈日治時期電力事業與工業發展〉,《臺灣學通訊》,113(臺北,2019.9)頁4-7。 陳佳德、傅希堯,《傳說:竹門秘境 微光往事》(臺北:台電,2018),頁95-96。
2023.12.23
揹著電桿爬山的人—— 讀《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
1970年代,登山風氣在臺灣的大學校園裡蔚為風行。據說,當時一些大學的登山社成員多達三百餘人,組團登山宛若部隊出動,規模十分嚇人。那時,「能高越嶺道」是頗受歡迎的一條路線,許多年輕人因此都有參與高山縱走、寄宿於「保線所」的經驗。 所謂「保線所」,實際上是台電「保線員」的工作站。學生們的登山路線,則是這些電業工作者長年背負著沉重資材、反覆行走於其間的工作道路。顧名思義,「保線員」的任務是要保養、維修台電的輸電線路。這群人以刻苦耐勞著稱,故也被稱為「保線牛」,意指他們古早農村裡辛勤做事的水牛那般勤奮。 「檜林保線所」的早期樣貌。(圖像來源:台電綠網) 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臺灣中部的深山裡,會有這樣一條橫越山嶺的輸電線路?這段故事,得追溯到1950年代起始的「東西輸電線計畫」。 戰後初期的臺灣,水力發電廠仍是臺灣電力事業的主幹。在美援支持底下,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建設橫越臺灣山區的輸電線路,使東部的剩餘電力可以向外輸送,支持全島工業的復甦。到了1960年代,當西部的電力建設發展起來之後,這條線路則反過來,將西部電廠的餘電送往東部地區。 1951年台電人員考察「東西線」的合影留念,刊載於台電內部刊物《勵進月刊》。(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山林裡的電塔與電線 無論是「東電西送」或「西電東送」,總要有人揹著電桿上山,把線路架設完成。之後,這些電線也需要有人常態性地進行維護。這條「舊東西線」與這群「保線員」,正是《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一書所欲介紹的故事焦點。 既是書寫山裡面的人與故事,兩位執筆者遂也在保線員的帶領之下深入山林進行踏查與採訪。這些親身訪查所獲,是本書精彩之處。全書共分八章,前半部分的四個章節主要討論舊東西線建設的歷史過程,後半部分則呈現人物訪談、相關故事。 「奇萊廟」是舊東西線上保線人員的心靈寄託。(圖像來源:台電綠網) 歷史部分除了有詳實的資料考證之外,執筆團隊也從台電人員的採訪當中獲得大量珍貴照片,呈現出保線員在山林當中的工作情況。結合各種品質極佳的歷史影像,使本書在視覺上豐富多彩,創造極佳的閱讀體驗。而為了更貼近本書所描寫的歷史現場,作者也深入山林,實際踏查保線員的日常工作路徑,使讀者能夠深切體會他們在山林裡負重跋涉的辛勞。 本書也訪談到東西輸電線工程當中的關鍵人物及其後代,並從中尋找到許多饒富價值的歷史線索。此外,全書還有一些別出心裁的有趣設計。譬如第六章〈守護高山電塔〉當中,有個小節的題名是「打開高山保線員的工具包」,透過各種各樣的物件,帶領讀者從細節認識保線員的實務工作。 東西輸電線計劃的歷史檔案。(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光被八表」背後的辛勤付出 本書的最末一章〈走過必留痕跡〉談論的是舊東西線的文資保存議題。做為臺灣戰後電力供輸的重要工程建設,這條輸電線路對於臺灣近代歷史而言具有深刻意義,相關遺跡如何保存、利用,是必須審慎思考的議題。 能高鞍部上的「光被八表」石碑在國內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不過,人們很少注意到這個高山上的紀念碑,述說的是臺灣電業發展史當中充滿汗水與淚水的一段故事。今天,臺灣這座島嶼擁有充沛的電力,已完成了「光被八表」的理想。但在這樣一種成就的背後,有許多為電力事業默默付出的工作者。高山上的保線員,也是其中較不受到注意的一群。打開《古道電塔紀行》,你會看見這群人在山道上努力不懈的身影,這群人的存在,也正是臺灣電力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迄今的關鍵原因。 *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 精彩段落節錄 保線菜鳥的震撼教育 對剛入行的年輕小夥子來說,訓練所課程結束後,實習才是震憾教育的開始。林茂山描述1957 年、18 歲在天池保線所實習大半年的過程,那份艱苦真是莫生難忘。 他表示,因為前一年天池大雪害,斷線嚴重,台電決定在跨距較長的電桿之間補強,增設電桿,他們這期共20 個學員便被分發到天池協助工程。時值六月,師傅帶大家擔著行李、工具材料從霧社出發,「我就一卡皮箱、一床十斤的棉被,一路徒步上山,本來計畫中午抵雲海吃午餐,」他笑嘆:「實在是毋知影自己的腳啊(實在是不知道自己的腳力啊),結果我們晚上八點才到雲海,一坐下就站不起來了!」 當時他負責縣界附近的補強工程,他說有的電桿設在高低落差6、700 公尺的溪底,「每天爬上爬下,不得了耶。」當初東西線建設完,在鞍部留有備用的注油木桿,學員們合力把木桿運到溪底。因為沒路可走、也扛不動,是用「溜」的,「我坐在杉仔(木桿的材質為杉木)上,順著土坡溜下去,溜到一半被石頭卡住,要趕快跟前面拉杉仔的人喊停,我下來把石塊清掉,再爬上去繼續往下溜,很危險啊!」 好不容易木桿就定位了,學員負責挖電桿孔、立桿,再由師傅拉線,「電桿孔要挖兩米四深,用鏟子、圓鍬、十字鎬人力挖,如果預備立桿的點遇到大石頭,位置不能改,就用炸藥炸開。」 每天在縣界揮汗工作完,走四公里回天池保線所,還得去砍柴、燒洗澡水給師傅,夜裡20 多人睡通鋪,約兩個榻榻米大的地方擠下三、四個人。辛苦中最感動的是八月十五中秋夜,「我站在縣界往花蓮看,彼端的山一座連著一座,白雲一綹一綹,像女人的頭髮一樣,講真的,實在好美。」他滿布皺紋的臉上揚起笑容,彷彿映照了那夜的月光。 就這樣日夜無休忙了幾個月,有次停電事故,調來2、30 個師傅搶修,幾天後搶修結束,林茂山說,當學員們眼見一大群師傅行李一背轉頭下山,想到自己已經幾個月沒回家,「攏流目屎(都流眼淚)。」當晚他們意志消沈,連下山到屯原扛米的路,都走得特別久,夜裡11點走到清晨都還沒回天池,「長官緊張地舉著火到半路接我們。」 天池的工程結束後,他們又被派到花蓮搶修木瓜溪一帶電塔,「離開那天沒菜了,臨時工幫我們帶的是『一粒便當配一尾魚脯仔』,中午走到奇萊保線所,那邊的班長特地摘瓜仔鬚(龍鬚菜)炒給我們吃,實在是有夠溫香!那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菜!」他更笑稱,坐車抵達花蓮龍澗時,「因為我們一拖拉庫學員已經幾個月沒剃頭,頭髮很長,穿的台電灰色制服又像是囚服,路人全盯著我們看,以為是哪載來的犯人。」 直到農曆年前,終於在花蓮發薪水回家,18 歲的少年家總算領到生平第一份薪水,一路慎重地將這兩千多元薪水袋緊抱胸前,坐好遠好久的車,返回台中的家。而林茂山這段半世紀前的實習回憶,也仍然是今日保線員工作的縮影。 (頁150-152) 保線所的生活點滴 前輩保線員鍾新瀛曾記述,天池保線所因地勢高風力強,房屋需用四方桁壓緊後再用鐵絲固定,中央有大門,屋內有高約兩米的燒柴烘暖爐,後方為廚房及浴室,左側榻榻米房裝備有載波電話及收音機。 載波電話也為原本漆黑無電的保線所,帶來光明。這得回溯到1960 年,沿線的明線電話改為利用乙線輸電線加裝載波電話,為了供應電話設備用電,才從各保線所最近的電桿接電、降壓使用。但最早接電量約僅500 伏安,《台灣電力發展史》中提到,載波電話用剩的電量大約剩餘200 伏安,雖只夠點數盞五瓦小燈泡,還是「令高山保線員萬分欣喜。」 因為缺電沒冰箱、也無瓦斯,早年保線員每天得砍柴生火煮飯,甚至自己種菜,且山上種出的高麗菜特別甜。米、肉就靠每人輪休從山下回來時補給,豬肉、魚多用鹽醃一醃,拉長存放時間。 夏天時,肉沒幾天就發出怪味,但花蓮線務段現任保線員劉世鉦半開玩笑:「豬肉變青色,照樣拿去魯啊、炸啊,我們阿美族吃了肚子不會壞啦!」 山上無自來水,保線員便設法用水管接山泉,在保線所內設儲水槽。但燒柴辛苦,洗熱水澡太奢侈,多用毛巾搓搓身體了事。「晚上很冷怎麼辦?蓋棉被啊。」保線員們個個硬漢性格,吃苦受凍都不抱怨。 南投分隊現任總領班潘信雄回顧,後來保線所接電的電量增加,雲海有了電熱水器、冰箱和冷凍庫。兩年多前東西線自奇萊以西停止輸電後,雲海無電可接,只好搬來發電機和汽油,晚上八、九點後就停用。早期的明線或載波電話都已走入歷史,改用無線電通訊,現在只剩電話桿遺跡。 葉義雄派駐的年代,保線所內配置兩個正式員工、三個臨時工,大家輪流煮飯,若有原住民同事就可「加菜」,「原住民會放陷阱抓山羌、山羊、野兔、雉雞等,煮湯加米酒來吃,」他透露,「論美味的話,一羌二兔啦。」 但即使保線所共五名同事,卻常因分別輪休、出差而只剩一人駐守,他哀嘆:「我常常早上看日曆,今天26 號,工作告一段落中午回到保線所,還是26號,晚上躺下來再看一次,還是一樣,感覺一天好長!」 舊東西線西段的退休保線員黃文松也說:「我常大半個月沒見到幾個人,倒是遠遠遇過身上有個白色V字的台灣黑熊,我怕,牠也怕,幸好牠停一下就慢慢走開了。」寂寞的日子還是要過,「偶爾有人下山帶報紙上來,就翻一翻幾天前的舊報紙。」退休領班李進添說:「工作結束就看看山,走一走,談談天。」 (頁174-176)
2023.12.15
電廠尾水與「漂漂河」:專屬於美濃小孩的在地遊戲
說起美濃,你可能會聯想到油紙傘或客家人、菸草產業或博士之鄉。不過,在地人都知道美濃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漂漂河」遊戲! 什麼是「漂漂河」呢?顧名思義,就是穿戴著游泳圈、救生衣,在流貫美濃的圳道當中順流漂浮、玩水消暑。這樣的遊戲活動由來已久,對於美濃的孩子們而言是共同的成長記憶。直到今天,「漂漂河」仍然是美濃當地的觀光亮點之一。每到夏日,總會吸引許多遊客前來參加這樣的遊戲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圳路平直、水流穩定的渠道,其實是高屏發電廠竹門機組的尾水!這座興建於1908年的水力電廠,是引入鄰近的荖濃溪水發電以後,再利用渠道將這些水排放至下游的獅子頭圳。這個排水渠道,後來不僅成為美濃當地農業灌溉的水源,也變成了孩子們的「漂漂河」遊樂場。 利用電廠尾水來灌溉農田,這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臺灣其他地方。像是宜蘭三星鄉的安農溪,其溪水來源也是蘭陽發電廠天埤機組發電後的尾水,當地居民也會利用這條河流來舉行泛舟活動。 看來,水力發電廠不只能夠發電,還能夠透過其它辦法,為人們的生活帶來樂趣呢! 美濃漂漂河上開心戲水的遊客。(圖像來源:高雄市政府觀光局高雄旅遊網)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陳佳德、傅希堯,《傳說 : 竹門祕境 微光往事》(臺北:台電,2018),頁175-177。
2024.02.05
「搖電話」的時代:東西輸電線與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
電話為什麼是用「搖」的? 你知道「打電話」的臺語怎麼說嗎?除了「敲(khà)電話」、「摃(kòng)電話」之外,過往臺灣人的習慣用語裡面,還有一種說法,是「搖(iô)電話」。 電話曾經是用「搖」的 —— 大約 20 世紀前期,臺灣人使用的電話機,經常是附有手柄的「手搖式電話」。使用者要搖動手柄來產生電流、發出鈴響,再請機房裡的「交換手」(接線生)幫忙接通線路,才能與遠方的另一部電話機連線通話。 不過,話機與話機之間,也可以透過專門線路直接連線,不必經由機房轉接。 20 世紀後期,台灣電力公司營運的「東西輸電線」(今稱「舊東西輸電線」),就曾佈建這樣一種專線電話。沿著輸電線配置的各個「保線所」都配置手搖式電話機,發生任何緊急情況皆可即時連絡。 「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也曾出現在早年臺灣的其他機構。圖中這部電話由交通部航港局典藏,當時被應用於燈塔的通訊聯繫。(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誰該接電話?先聽鈴聲再說! 問題是,這種封閉式電話系統裡,只要搖動任何一部話機的手柄,線路上的每部話機都會同時響鈴。那麼,究竟該由哪一個保線所來接起這通電話呢? 其實,手搖式電話的鈴響長度,可以藉由轉動手柄的幅度來加以控制。若將長、短鈴聲的各種組合,設定為各個保線所的通訊代號,就可以識別每通電話的聯絡對象了! 2018 年,台電公司清查「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文化資產時,曾採訪多位退休保線員。其中, 1970 年代支援過東西輸電線維修保養工作的楊儒溝先生,就提到各個保線所的電話鈴代號: 舉例:一長是天池,一長一短是雲海,一短一長是廬山這樣。曲柄桿轉久一點是一長,轉少一點是一短。 另有幾位前輩,也談及東西輸電線上的電話使用情形。據說,早期的「名間保線所」是整個電話系統的總聯絡站,「每天早上 7 點鐘,領班要跟名間保線所聯絡,確定線路是通的」。有些時候,山裡的猴子還會把線路拉起來玩耍,造成通訊上的困擾呢! 台電公司典藏的「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早期這類電話都具有相同的黑色外觀與流線造型。(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流行於 1950 年代的日本製「 4 号電話機」 過去配置於保線裡的「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 」,已成為台電公司的典藏文物。所謂「 4 号電話機」,其實是 1950 年由日本電信省推出的一種標準化規格。根據電信史研究者楊振興的說法,「 4 号電話機」相較於 1933 年推出的「 3 号電話機」,其改良之處在於「送話器和送話器採用輕質鋁合金製薄膜,靈敏度高了,頻率響應也較佳」。 在 1950 年代的日本,「 4 号電話機」是市場上的主流規格,主要由日本國內的六家公司(包括我們所熟悉的日立、東芝、富士通等等)負責生產。其中一些磁石式電話也被進口到臺灣,之後也陸續產生許多國內的仿製版本。這類電話經常被應用於各種需要專線聯絡的場合,東西輸電線的線路維修保養工作,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另外,在戰後初期臺灣的警用電話系統當中,也能見到「 4 号 M 磁石式電話機」的身影。 日本東京「逓信総合博物館」所展示的「 3 号電話機」與「 4 号電話機」。 (圖片來源:Haruhiko Okumura@flickr, CC BY-NC 2.0) 物件裡的臺灣電業史 20 世紀後期,家用電話逐漸在臺灣普及。人們所使用的電話開始有撥盤、按鍵,也開始不再需要「交換手」的人工操作,就能自動接通另一部電話。隨著時代變化,磁石式電話也慢慢消失在人們的視線與記憶之中。 同樣的,隨著通訊技術演進,東西輸電線上各個保線所曾經使用的磁石式電話,也逐漸被無線電話、衛星電話所取代。古舊的手搖式電話於是被拆卸下來,塵封於倉庫深處,直到近年才被重新發現,並妥善保存。 手搖式電話如今已經不再被用於傳遞聲音,卻能夠告訴我們許多關於東西輸電線的歷史訊息。而在整個臺灣電業史極其豐富的文物遺存當中,必然還有更多故事,等待我們細心探究、努力找尋。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台灣電力公司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四大電力場域文化資產清查委託服務案」舊東西線輸電線路期末報告》,2019。 林欣誼、陳歆怡著,《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台電,2018。 楊振興,《話筒裡的台灣:從摩斯電報到智慧型手機》,臺北:獨立作家,2016。 粉紅色小屋,〈【台語原來是這樣】電話要用「打」的,還是用「叫」的?〉,「故事 Storystudio」網站,2015。
2025.07.21
【臺灣百年電業史話05】電線桿
1926 年 10 月 10 日,是臺灣史上值得銘記的日子。這天,留學東京的臺籍西畫家陳澄波,成為第一個以繪畫作品入選日本「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的臺灣人。 值得注意的是,陳澄波的這幅《嘉義街外》(嘉義の町はづれ),描繪了故鄉嘉義的街道風景。而在畫面中,我們會發現一個醒目的現代化元素,也就是排列在街道兩旁、一根根矗立的電線桿。 陳澄波首度入選的《嘉義街外》目前僅有照片留存,但畫面裡的電線桿依舊醒目。(圖像來源:LY@Wikipedia) 陳澄波與嘉義市的電力建設 若試著翻查陳澄波的其他畫作,我們會發現他的城市風景畫裡,電線桿是個經常出現的街景物件。在他第二次入選帝展的《嘉義街景》這幅畫裡,電線桿更是被擺在了正中央,宛若刻意強調它的存在。 一個生活在日治時代中期的臺灣畫家,為什麼對於電線桿會如此著迷?關於這點,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從陳澄波及其同時代人的成長背景,來做些推敲。 陳澄波在 1895 年出生於嘉義,那年日本也正好開始統治臺灣。因此,在陳澄波的成長過程裡,想必目睹了這座城市裡各式現代化建設的逐一出現,電力設施亦是其中之一。 1913 年,當「嘉義電燈株式會社」在當年秋天開始向整座城市供電的時候,他正好離開故鄉到臺北求學。可以想像,當他每一次趁著學校假期回到嘉義,發現熟悉的故鄉街道,竟然一處處接連樹立起電線桿,並且在夜晚亮起了街燈,那樣的巨大轉變,或許也在他心裡也留下了強烈的衝擊感吧! 陳澄波1927年的作品《夏日街景》,呈現當時嘉義市中央噴水圓環附近的景象。(圖像來源:開放博物館) 城市風景畫裡的電線與電桿 有趣的是,在陳澄波的風景畫裡,電桿雖然醒目,電線卻被刻意省略掉了。身為畫家,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要描繪的景物,也可以略去那些對於構圖、美感等等較不利元素。 當然,每個畫家的選擇不見得相同。我們看同時代的日籍畫家小澤秋成,他的《臺北風景》裡除了同樣引人注目的電線桿以外,也隱約能看到橫過天際的電線。小澤秋成對於「電線桿」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曾在一次採訪當中說道,許多人總認為電線桿看了礙眼,但他卻想要透過電線桿把「線條的魅力」帶進畫面當中, 另一位畫家鄉原古統描繪臺北城裡熱鬧的街道,電線在十字路口上空的縱橫交錯,使畫面顯得更為鮮明。如同畫裡所呈現的那樣,越是熱鬧的城區,電桿、電線的建置也越趨密集,對於城市景觀的影響也就更形巨大。 1931年小澤秋成的作品《臺北風景》。(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鄉原古統筆下的臺北榮町,圖中的街道是今日臺北市的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圖像來源: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國家文化記憶庫) 電桿、電線與城市生活 電線與電桿的過度密集,有時也會引起民怨。 1890 年,日本東京的電力建設正如火如開展,《東京日日新聞》的一篇報導卻說道,這座城市裡的許多老百姓已開始覺得自己像是生活在蜘蛛巢裡(東京市民は蜘蛛の巣の中に生活し居るかと怪まるる程なり),舉目四顧,全是密密麻麻的電線。這篇報導刊出的時間點,距離東京地區的第一盞電燈亮起才不過短短八年。從歡欣鼓舞到表露嫌惡,東京人對於電力建設的態度轉折,可謂極其迅速。 日治時期,當電線桿剛剛出現在臺灣人眼前的時候,或許也還沒那麼令人反感。街道上出現電線桿,代表鄰近家戶已經能夠向電力公司申裝燈泡、電扇,走進現代生活。 1924 年,新竹仕紳黃旺成的新房子剛蓋好不久,舉家喬遷的第一天,他便趕快要找工人,自費裝設電線桿,讓新家可以點燈。 話雖如此,電線與電桿的設置,也不全然與好事相關。居住在豐原的臺籍仕紳張麗俊,則在 1936 年 7 月 31 日參加朋友的喪禮。但他發現典禮會場緊挨著街上的電桿與電線,導致帳幕難以張開,輓聯也沒辦法被懸掛起來,令他著急的不得了。 另一位著名仕紳林獻堂則在 1929 年 12 月 21 日的日記裡,寫到四弟林澄堂的妻子到臺中看牙醫,回程途中乘坐的車子卻不慎撞上電線桿,才剛治了牙痛,卻又傷了臉頰。這種汽車撞上電線桿的車禍事件,在日治後期的報刊屢見不鮮。比如《臺灣新民報》在 1938 年 4 月提到彰化一輛卡車撞倒電線桿,導致整座城市瞬間停電。 1940 年 2 月,一篇報導則說高雄有兒童巴士為了閃避電線桿而不慎翻覆。隨著電桿佈設的密度越來越高,這類與電桿相關的事故,自然也就越趨頻繁了。 電線桿廣告也能收費? 不過,密集設置的電線桿,也可能在城市裡發揮其他功能。日治前期,由總督府作業所建設的電線桿,就曾經設置廣告版位,讓商家付費宣傳。只要付一圓不到(約等於當時許多臺籍工匠的一日工資),就可以在市區裡的某個電線桿上張貼三個月的廣告,聽起來頗為划算。 有個例子是日治初期開設於臺南的知名藥局「愛生堂」。 1910 年,當臺南市的電線桿開放廣告申請以後,他們便率先買下不少版位。透過密集的電線桿,讓自家廣告頻繁出現在群眾眼前。 愛生堂在廣告方面非常捨得花錢。根據報導,這家店鋪剛開幕的時候也曾砸下重本,組成廣告隊伍,在臺南市區整整遊行了一整個禮拜。當時的報導說道:這種事情在本地前所未見,愛生堂可說是首開風氣。同樣的,當「電線桿廣告」這種宣傳管道出現以後,愛生堂也依舊要搶在前頭。至於這些電線桿廣告究竟為他們帶來多少業績?恐怕也只有業者自己知道了。 - 距今不過二、三十年前,臺灣各地的電線桿也曾經被貼上各種聖經標語、房產廣告。不過,隨著電纜地下化工程的逐步開展,電桿與架空線路逐漸減少,前述的雜亂景象也變得少見。 從陳澄波成長的時代開始,在臺灣密集建設的電桿與電線,曾是一道醒目的城市風景。如今,那樣的景象正從我們的生活裡逐漸退場。至於與之相關聯的歷史記憶,則仍舊留存在種種的文獻材料當中,等待著我們仔細找尋。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蔡承豪,〈側寫嘉義電力發展史從陳澄波畫作中的電線桿談起〉,《故宮文物月刊》,第386期,(臺北,2015),頁90-102。 〈愛生堂藥房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23日,第5版。 〈電柱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5月10日,第4版。 〈電燈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8月21日,第6版。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36年7月31日。
2025.11.30
獨木舟上的歷史追尋:讀《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
2015年,臺灣前輩畫家陳澄波的畫作《東臺灣臨海道路》,在日本山口縣防府市的圖書館被找了出來。這幅畫描繪的是1930年的清水斷崖,以及匍匐於斷崖底下的一條狹窄道路。 時至今日,畫裡的道路早已經過改良,並以「蘇花公路」之名廣為人知。不過,在陳澄波的時代,「臨海道路」的大約也就如同畫中所呈現的那般狹窄。若有車輛往來,大約也只能勉強通行。換句話說,蘇澳與花蓮之間的陸路交通,在日本時代雖然已有長足進步,但始終無法達到「貨暢其流」的境地。 陸運的能量既然有限,殖民政府只能看向海洋。於是在1931年,「花蓮港」的築港計畫正式展開。有了一座大型的現代化港口,花蓮的人口與產業規模,勢必將有大幅成長。為了因應這樣的發展趨勢,電廠的布署也得及早進行。加上1930年代後期的戰爭暴發,重工業的電力需求更是迫切——上述種種,即花蓮地區水力發電會在日治末期急遽成長的主要原因。而所有這些在戰爭期間進行建設與規劃、並且在戰爭結束以後持續進化的各個電廠,大抵也就是李瑞宗在《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這本書裡,所欲尋訪的對象。 木瓜溪的風貌。(圖像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山林踏查的書寫傳統 《後山電火》與李瑞宗在「臺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裡出版的前一部作品《大甲溪:水電俱樂部》頗為相仿。兩者的寫作方法,皆以自然環境與歷史現場的踏查為敘事軸線,再從文獻當中尋找故事線索,並剪裁其原文,補足每一段故事的背景脈絡。 山林與河流的踏查,某種程度亦可說是台電自身的書寫傳統。由於早期臺灣水力電廠的開發建設,工程位址經常都在山區,許多台電員工都有披荊斬棘、開荒闢路的踏查經驗。其中一些人更把這樣的經驗寫成文章,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見聞紀錄。 水量豐沛、落差大的木瓜溪是東部發電廠的動力泉源。(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譬如1947年,台電員工李式中等人為了擬定東部系統的「全盤方針」,遂乘坐著汽車、越過了當時仍然充滿險阻的沿海公路來到花蓮,針對既有電廠的運作情況進行視察,李式中並且將這次的旅行經驗寫成〈東行追記〉,刊載於當時台電的《勵進月刊》。這趟旅行,他們置身於立霧溪,不禁心折於太魯閣的鬼斧神工;來到木瓜溪,則嘆服於「怒馬奔放」般的湍急水勢。 相較於今日發達的交通情況來說,1947年的立霧溪與木瓜溪,仍不是輕易可以抵達的地方,故而在當時候,李式中等人的震撼,仍可說是相當稀罕的經驗。其實,在後來的時代裡,台電或者為了擴增水力發電的系統規模,或者為了完善全島的電力網絡,仍有許多員工持續地深入山區,並且也都曾經在內部刊物當中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本書引用了其中一些台電前輩的山林紀行,對照作者自己所做的現地調查紀錄,兩相對照,頗有一種穿梭時空的趣味。 1954年的東部臺灣地圖,呈現出花蓮境內的水利工程。(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 正文當中,作者經常大篇幅引用原始文獻。這些「原汁原味」的引文段落,或者摘譯自日治時期的報紙,或者轉錄自戰後出版的台電刊物與相關書籍,及零星的檔案、手稿等等。所有這些材料並非輕易可以得見。作者揀選相對易讀的史料,並刻意保留其原文樣貌,能夠幫助普遍讀者循著當時代的語言,認識當時代的故事。 本書收錄的人物採訪,仍沿襲作者一貫的書寫風格,不囿限於重複而平板的問答框架之中,而總是能夠帶領讀者看向一些別有意趣之處。例如第四章〈從瀧見至龍澗〉,寫到四名在龍溪壩值班的台電人員,作者不費筆墨,僅只簡要地列出電廠裡的三班值勤排程。藉由這類細節,作者直白地展示了守壩人的日常工作節奏,使讀者對於這一職業能夠迅速建立起認識輪廓。 為銅門發電廠提供發電用水的水簾壩。(圖像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每個章節末尾,皆附有大量印刷品質極佳的彩圖,除了呈現工程藍圖、歷史檔案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今昔影像對比。所有這些圖像材料,適切地配合章節內容,與文字描述相互補充,使全書讀來更顯生動。 本書的最末一章,作者忽然帶領我們來到清水斷崖的近海處,乘上獨木舟,遙望東臺灣海岸線上各個河流的出海口。此情此景,不免使我們想起1930年,陳澄波在《東臺灣臨海道路》所描繪的景象。在那幅畫裡,同樣有一葉扁舟,飄盪於藍色大海。 電廠歷史的百年追尋,帶領作者循著河流溯源而上,涉足於山澗與溪谷之中,但所有這些河流終究要滾落大海,故而作者也將此行的終點設定於太平洋上。從山林到海洋,本書可說是一趟跋山涉水的閱讀旅程。若能跟上作者的腳步,相信讀者也能在跋涉之中,盡覽後山電火的故事,以及所有那些故事裡的景色風光。 *對於本書有興趣的讀者,趕快點擊連結,到「國家網路書店」下單購買吧! 精彩段落節錄 木瓜溪畔的「勤行報國青年隊」 臺灣總督府以瀧見訓練所為名,其實是拓寬改修能高越道路,完成可以通行車輛的自動車道路,自1941年開始,規劃以7年期間,總經費930萬日圓來執行。1942年5月15日在瀧見舉行訓練所入所式,《東臺灣新報》亦曾報導。 花蓮港瀧見訓練所建於距離花蓮港30公里的深山內,位於木瓜溪與奇萊溪交會、標高300多公尺的懸崖上,是總督府引以為傲的勤勞報國青年所之一。訓練所共有四棟營舍,所內聚集從全島各地被選召的310名青年精銳,每天奮力地進行訓練。1943年8月22日,這座地處偏僻的訓練所,自設立以來首次迎接總監西村文教局長及同行記者到訪。以下為訪問紀實。 右手邊幾十丈高的懸崖溪谷變得寂靜無聲,甚至略顯詭異,淺灘隆隆地濺起白色水花,一種不似死亡般神秘的冷意迫近眼前。由花蓮港的市街往北,在沿著能高越山路綿延約16公里,木瓜溪溪水飛濺的山峽中,有著一座培育皇民、鍛鍊身心的青年道場,即「總督府行動報國青年隊花蓮港訓練所」。 此訓練所自前年(1941)7月7日設立以來,已歷經六期共1,782名訓練生,當前的第七期訓練生亦是奉公精神高昂,全心全意地鍛鍊身心。訓練所位於瀧見駐在所後方。沿著高聳令人不寒而慄的斷崖旁所開鑿出的狹窄山路前進,走過石門橋單薄的八番線吊橋,就可以看見訓練所的營門。炸藥爆炸的轟鳴響徹山間,首先讓人感受到工程的偉大,接著受到恭敬地舉著鏟子的衛兵迎接,穿過大門之後,木造的簡樸營舍與一片翠綠相映成趣。 訓練所的勞動作業現場,為總督府國土局道路課正在進行的工程,即橫斷中央山脈,連結臺中州霧社及花蓮港廳銅門之能高越道路蜿蜒70公里大型工程。此工程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第三期⋯⋯延續到第六期,完成若干部分的挖鑿。施工地就在訓練所向沿60度陡坡走約4,000公尺處,是岩層相當堅硬的山腹部分。 在天長大斷崖附近,烈日高照,白雲來去,鳥跡不至的山嶽地帶,要緊貼山壁削鑿岩層、填封溪流,在懸崖上施工,稍有差錯便會墜落千丈深谷。訓練生都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晒成紅銅色的身軀佈滿沙土顯得黝黑。 訓練所規定5點半起床,比其他的訓練所要早半小時。巴托蘭峰上雲層在黎明之時尚顯微暗。310名訓練生編列為三個中隊,六個小隊。他們在近似深山秘境的崇山峻嶺中的訓練生活,首先是5點半吹響起床號,接著早點名、神前行事、朝禮、早餐都要在7點前完成,然後7點立刻投入施工作業。訓練前期的作業時間為6小時,現在則為8小時,激烈訓練不曾間斷。 一天的作業在5點收工,晚禮結束後沐浴,6點吃晚餐,7點開始有一個小時的學科講習,公民科、國史(歷史)等學科結束後,就是神前行事(行拜禮,祈求安全),接著8點40分有晚點名,9點半準時吹響迴盪入夜深山的熄燈號,結束一整天的勤勞訓練生活,這就是1941至1943年在瀧見山區發生的故事。 (頁122-124) 兩代台電人 1987年6月,新天輪工程處成立,東部電力處有許多工程人員調往支援,同年8月,東部電力處改為東部發電處。經歷了多年的開發與建設,東部的水力發電工程暫告一個段落,平穩供應著無數家庭與工商百業的用電需求。 1993年10月28日下午4點3分,正在進行併聯發電竣工試驗時,洞內突然發生爆炸,不幸造成6人死亡、25人受傷,往生者其中一位褚副處長是臺北工專畢業,為人篤實認真負責、心地非常善良,竟遭此不幸,讓人悲慟不已! 同事三年之褚金松君努力向上,工作勤奮。猶記褚君背負儀器盒如走方郎中,走遍各電廠,測試進水鋼管開裂的情景。年前從台電月刊得知,褚君因公殉職消息,不勝扼腕。 ——壽紹漢,〈回憶四十六年前 新竹變電所來的實習生台大人〉,《台電月刊》,404(1996),頁62-63。 褚金松,嘉義市人,1933年出生,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嘉義初工電機科畢業後,先至嘉義變電所服務。1951年調立霧發電所擔任技工,那年他18歲,1953年調東部發電區管理處,那年他20歲,加入花蓮信義長老教會,認識同為教友的明義國校老師高麗子。在花蓮待了5年,考上台電的獎助升學班,到臺北工專唸書。25歲那年結婚,28歲回至東部發電區管理處,調派龍澗發電廠服務,歷任工務員、計畫股長、檢驗隊長,1988年調派新天輪工程處電氣課長,後來升任副處長。高麗子為花蓮師範學院畢業,國語、算術、音樂、美術都教。褚家有鋼琴,兩個女兒都會彈,長男後來當老師,長女也當老師。農曆過年時,褚金松夫婦帶著2男2女回嘉義看祖父母,那裡現今還住有二姑。 褚信杰1969年出生,差大哥10歲,在家中年紀最小,不過不會彈鋼琴。因為是老么,雖然備受寵愛,較不循常軌,他覺得自己是父母意外所獲,並非預期所生。 「爸爸長年不在家,我們好像是單親家庭。」 褚信杰自花蓮高中畢業後就沒升學,在外打工。當兵回來後,到一家美術燈公司工作,參與生產與組裝,領有冷凍空調的證照,對於電氣並不陌生。1993年10月28日,新天輪工程在試運轉時發生爆炸事故,丁世凱廠長、褚金松副處長因公殉職,那時褚信杰24歲。意外來得如此迅急,全家陷入愁雲慘霧,媽媽很悲傷,將爸爸葬在佐倉公墓。 1994年褚信杰進入東部發電處電氣股工作,受到張添和、林明輝兩位領班的傾囊相授,5、6年後對於電氣技能才順手。他不斷學習精進,18年後的2012年,升任電氣課領班。 「他們是我的師父啊!」褚信杰充滿感謝地說。 電廠的發電機功率高、量體大,外面遇不到,學校未必教,就要師徒式的耳提面命,才能增長經驗。張添和1934年次,花蓮中學初級部畢業,歷任立霧裝機工程處、銅門工程處、龍澗工程處,後來留在東部發電區管理處維護課電氣股工作。本書所附1959年4月21日〈蔣中正總統與龍澗工程處人員合影〉這張照片,張添和也在其中,裡面人物多靠他的指認,方得解析。張添和1990年擔任領班,1994年退休。林明輝1942年次,1965年進入東部發電區管理處工作,在銅門電廠一待就是21年,1986年調任維護課電氣股,1994年擔任領班。兩位諄諄長者在40多歲時還去進修,取得高工畢業學歷,俾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更加精進。 在台電的工作穩定後,褚信杰結婚要買房子,買在哪裡呢?媽媽資助他,就買在佐倉附近。那時媽媽已經退休了,每天都來串門子,然後就離去,他隱約知曉媽媽的心意。十多年前,媽媽因胃癌過世,媽媽也葬佐倉,就在爸爸旁邊。 佐倉的家離爸爸的墓有多近? 下班之後,我刻意到褚信杰家坐一坐。 他帶我步出家門,向左一轉,根本不用5分鐘,根本不到500公尺,就到褚金松的墓。我想,高麗子一定常來徘徊,每天都來看兒子,每天都來陪先生。春去秋來,花開花落,許多許多話,或私密,或叮囑,或寄託,都還來不及說⋯⋯。 (頁179-182)
2023.12.15